引
尽管有预感要来沙窟村任第一书记、工作队长,当我拿到县里批复任职的文件时,还是在办公室独自待了许久。
我出身农家,对农村人、农村事、农村景并不陌生,对乡村振兴有着深切的期盼和满腔的热情。而令我焦虑的是,即将下派任职的沙窟村,是一个有着相当厚重文化的古村落。
乡村要振兴,文化必振兴。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古村落,如何经过我,一个“太行小镇”作家之笔头、摄影人之镜头,进行生动性、鲜活化、思考性的整理与传播,助推乡村文化的复兴?
我曾多次从沙窟村路过,总是小心翼翼,生怕惊扰了壶邑“祖先的梦”!多次仰望苍松翠柏包裹着的古圣山(沙窟村乡亲称为“庙垴山”),却不敢攀登,生怕浅薄的文史功底,无法解码这里所曾发生的考古事件、人文故事、玄妙传说!
近年来,我作为太行山地乡土作家兼摄影师,已开始实施自己的“百村(项)百篇百万图文”的文创公益行动,至今,已先后为16个有特色的乡村(项目)进行了图文推送。壶邑名气很大的古文化村——沙窟,自然在靠前推送之列。今年初,我就着手查找壶地史志书籍,期盼能够查找到更多的与沙窟地域古老文化有关的文字、图片,但我很是失望。收集到的素材十分有限,根本无法使我对沙窑地域古老文化形成完整、清晰的文学创作,影像拍摄支撑。
正当这个文创计划被搁置时,2023年4月初,我到沙窟村任职。巧合的事情、顺遂的缘分,莫非是我的虔诚“感动”了上苍?使我能以一个壶邑“文化世家”出身的文化人,对沙窟地域的厚重历史文化进行全新的文学解读。
七亿年前的“鱼儿”会说话
春季的古圣山,风儿裹着温厚的气息,迎面吹来。满山的松柏正由冬季的墨绿向春季的黄绿过渡。山坡上盛开的连翘花,在风中摇曳。此刻,我独自行走在山路上。一簇枝条上开满了小黄花的连翘,吸引了我。一米高的枝条上,盛开的小黄花竟然有50多朵!因花开较多,细细的枝条被压弯了腰,顺势在风中摆动,风一停,就又归回原位。这种遍布壶邑、不限地域、扦插生根、早春开花的植物,之所以被评定为壶关的“县花”,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生长过程像极了坚韧、厚道、睿智、奋进的壶关人民!

登临古圣山顶的平台,极目远眺,诸峰环合,峰峰相连。在这个高地上,不知是松柏阻挡了风势,还是松柏加强了风力,松涛声声急,从耳边呼啸而过!这呼啸声中,我仿佛听到了从远古海洋传来的风吹大海的涛声!是我的错觉吗?不是!这涛声是从七亿年前传来的!这涛声中传递着远古海洋生命的图景:海平面一望无际,海水洁净透明。海洋里,一群群鱼儿、海螺正在自由游动。

然而,现代人“我”的突然造访,打破了它们的游动节奏,鱼儿、海螺都在定睛看着我这个立在岸边的“怪物”:怎会有长相这样的“鱼儿”?站在海岸上而不是游在水里,浑身没有一片鱼鳞却穿着迷彩服,“鱼眼”不是长在脸的两侧而是长在正前方,还特别大!……在远古鱼儿的眼里,我就是来自别处、长相怪异、供“鱼们”观赏的“动物”耳!

在鱼儿的一片“议论声”中,我一下子“穿越”回当下,蹲下身子才发现,自己脚下的山坡上,遍布着星星点点的鱼化石、海螺化石!距现代海洋有着千里之遥的古圣山麓,怎样会有成片的远古鱼儿、海螺的化石?我想到“沧海桑田”。此处裸露的青石上留有的大量化石,说明在远古时期的太行山地域一定是汪洋大海,古圣山地域一定是大海中最深的地方。鱼儿、海螺死亡或者遇到地质运动后,沉底被沙石流覆盖,经过漫长的地质物理化学反应,形成了化石,后来又经过地球新的“造山”运动,太行山地域从海底抬升出海平面,并且经过不断抬升,形成了今天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千里太行山脉,海底之处的古圣山地域也被同期抬升至太行山脉的东南山巅。
太行山脉地域就是远古海洋动物化石的集结地!若干年前,我曾多次去过位于山西壶关太行山大峡谷的红豆峡景区,看到了地质运动时滚落在峡谷谷底的巨石上密布的鱼儿化石,我触摸它们,想用我的体温温暖它们早已“冰凉如石”的心!今天,我又一次见到这些“鱼友”,心情十分激动。
小心翼翼地在古圣山麓的“石鱼坡”前行,生怕惊扰了它们跨越了上亿年的宁安与不朽!这些形态各异的鱼化石、海螺化石,有的蜷缩着,有的扭曲着,有的只有身躯没有头部,有的仅有头部而没有身躯。我紧靠着它们坐在青石上想:它们“坐化成石”从远古走向现代、露出地表,让我在沙窟地域亲眼看到的概率有多大?我与它们的相见,应该是一场多么难得的小概率缘分事件啊!
整个下午,我就静静地坐在这里,忘记了时间、地域、物种差别,与亿万年前的鱼儿“对话”,时起时落的春风与松涛声是对话的“背景音乐”。它们的“鱼话”我时而听懂、时而听不懂,但能有机缘“听到”,本身就是一场跨越千古、穿越亿年的“心灵约定”!
这时,沙窟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王宁打来电话,打断了这场“约会”:“平哥,听说你上了石鱼坡了?哥,你用矿泉水浇一下青石板上的石鱼,看看哪一条动得最欢,就是和你最有“情缘”的鱼……”我应声而做,果然看到青石板上的一条条化石鱼在浅水里变得“活泼”起来!我看到其中一条身材修长的鱼儿摆动得最欢,最优美,这大概就是传说了很久的“美人鱼”吧!
这条鱼游着游着,就游进了我的心海……
一万年前先人的灶台冒着“炊烟”
从小受文化人父亲的深切影响,我对人类历史特别地关注,对“人类的起源及进化”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北京猿人复原图的雕像,我经年不忘;仰韶文化遗址发掘的石斧、石铲和陶器残片图片,我记忆犹新。

1970年代后期,我在壶关县一个叫“谓理”的山村读小学,我家的房背后就是山坡。我时常在山坡上捡拾一些形状如刀状的石铲、如红缨枪头状的尖石拿回家,让父亲甄别这是不是古人使用过的“石器”。父亲看后说:“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,没有打磨过的痕迹,不是早期人类使用过的石器。”年少的我并没有死心,仍然不停地在村子周围的山坡、河沟捡拾些特殊形状的石头。但直到我转学至县城读书,也没有在村里找寻到一块被古人打磨使用过的石器。童年经历,促使我成年之年成为“石痴”,每遇奇石必捡拾,因为我相信,总有一天会捡拾到一块古人曾打磨并使用过的石器!

1989年,我读高中,父亲在县文化馆当馆长。那年春天的一天,他回家后告诉我,黄山公社沙窟村的灰砖窑场出土了经过古人打磨并使用过的石器,有石铲、石斧、石核,陶鬲、陶釜,还有动物骨头磨成的锥子。太行山巅的壶关,还真有这样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!
沙窟村距离我的老家谓理只有七八里地。小时候,我跟着母亲还去沙窟村赶过“八月初一”的庙会,村子在一处高高的平地上,没有成片的森林、草地、河流。高中时期,我的《历史》学得最好。我知道,新石器时代大约从一万多年前开始,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4000多年。历史课本中对新石器时代的“仰韶文化”进行了重点介绍。考古研究发现,“仰韶先人”的聚集地一般选择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,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,因为这里土地肥沃,有利于农业、渔猎,生活用水且交通也很方便。显然,今天庙垴山高地的沙窟村砖窑场,并不具备古人类生活的地形地势条件,但我相信,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沙窟地域,一定是个森林茂密、溪流潺潺、鱼儿欢游的绝美之地!

1983年,因沙窟村灰砖窑切岸取土,在黄土崖中开始出现一条烧灰带,灰带里陆续发现有陶盆、陶罐的碎片。砖窑取土的乡亲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,因为他们这些年取土总或多或少,或密或疏地发现灰带中的瓦砾残片。这天,沙窟中学(当时在沙窟垴玉皇七佛庙里办学)任教的宋有泉老师发现这一情况,觉得此处应该是一处古人类生活的遗址。急忙上报县里。之后,上级文物管理部门共划定19000多平米的区域为遗址保护区,对发现的有考古价值的文物,先后被上级文物部门收藏保管。1990年,这里正式被确定为“新石器时代和商周遗址”。1996年又被列为“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从考古中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石铲、石斧、以夹生砂为主的陶器到战国时期的铁锸。据此,沙窟村有人类居住的历史可推断至一万年多左右。壶关县歌《英雄壶关》里的“沙窟垴有咱祖先的梦”的歌词正是出于此!

这里发掘出的文物到底“长”什么样子?采写这些文字时,我本想去县文博馆观瞻一下,但是不巧的机缘,使我无法目睹万年前的古先人曾使用过的物件,还好,我联系了县里的文管部门,看到了县里收藏的几件藏品的图片,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写这些文字的兴致,我似乎在为自己的“石痴”爱好而续写新的故事!
研究推断古人、古事、古代是很有趣的事。2023年4月下旬,我在村委副主任、遗址保护责任人栗兰则大姐的引导下,第一次走进这个遗址区域。我虽过了对新事物好奇的年龄段,但还是期望在遗址区内能发现些什么,会发现些什么!我低着头,仔细找寻可能会出现的石块、陶片、瓦片,结果一无所获,可见当年考古发掘有多彻底。倒是在这一区域的地后岸发现一些天然形成、有些特殊造型的“类姜石”,其中的“重大捡拾”当数捡到了一块类似“中国地形图”样的“类姜石”。我稍加修整,就变成了一个粗加工制作的石工艺品,现在就摆在我的书架上,权当是一次“考古实践”的收获吧。

第二天,一场不期而遇的“倒春寒”大雪飘落,将古圣山高地“新石器时代和商周遗址”厚厚覆盖。这场雪,将我昨天观瞻时留下的脚印抹去,也将一万多年的时光抹去,“地下”古先人的生活又回到了原先的样子。我仿佛看到雪地后岸的窑洞里升腾起了白色的烟气:那是古先人在用最原始的陶鬲烧水,在煮狩猎回来的山羊。另一个窑洞里的先人正在用树枝串着羊肉块,在烤肉吃。我似乎闻到了烤肉的香味,是近来很火的“淄博烧烤”的那种肉香味!
这时,妻子打来电话问我,今天中午吃什么饭,我不假思索地说“清水煮羊肉”吧!至少,今天这顿饭,我与“古先人”吃的一样!
北魏石窟中的“无解谜团”
我的父亲曾长期在县文化系统工作,他特别关注全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,他健在时拍摄了大量的壶邑现存的、已经消失或正在损毁的古庙、古院、古迹胶卷图片。1988年,他拍摄并撰写的《耍“龙灯”的传说》图文被《中国民间故事》刊登,使壶邑的“龙灯文化”蜚声三晋。曾记得,他当年也拍摄过一些沙窟村玉皇七佛庙的图片。
近些年来,特别是2017年,我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之后,也加入到保护全县“非遗”的拍摄、记录与保护的队伍之中,力争用相机的镜头和手中的笔头,为我的家乡留下些可供后人查阅的文献性图文资料。我每年大部分的休息时间都在这样做!把每一张图片进行编码处理,标注拍摄时间、地点、古建、物件的尺寸等要素。我很享受正在做的公益事项。但结果是:近乎疯狂地拍摄、记录的速度,远远赶不上因自然或其他因素损坏的速度!几乎每一次拍摄,都无比遗憾、无比惋惜!

入职“文化古村”沙窟伊始,我就开始对于古圣山巅的元代建筑玉皇七佛庙,进行“深潜式”文字采写和影像调查,尽心、尽力、尽情地将这座有着700多年建筑史的建筑文化故事写好、写深、写生动。我时刻准备吃苦、准备挑战自己的文字功底!我住在村委的宿舍,好几个夜晚无法入睡,在空灵的时空里,我与玉皇七佛庙的故事传说水乳交融!有些片段,我甚至感觉自己就是故事中的主角!
清朝道光版《壶关县志》记载:西室供奉玉皇,东室供奉七佛。短短12个字的记载,无法还原事情的原委。又看到省文物部门的考证,此为北魏(386-534)年间的石刻。历史书籍告诉我们,信佛的北魏拓跋氏政权先后开刻了大同云冈石窟,太原西山大佛,而且在从大同迁都河南洛阳的必经之路——上党地区刻成了沁县南涅水石刻、长治县羊头山石刻群等。比对发现:上述地区的佛像石刻都是“地面刻”“悬崖刻”,而地处山西壶关沙窟的沙石窟却是“地下刻”!未去玉皇七佛庙之前,我曾想:这块方丈有余的砂石是北魏时期从别处运来、安放至此雕刻而成的。但我完全想错了!当我与沙窟村乡土文化人曹胖孩先生一同上山进庙,仔细查看后发现,整座玉皇七佛庙都坐落在一块5米见方的淡黄色沙石上!
“地面刻”“悬崖刻”相比地下挖窟而刻的难度低。但是,面对这座地下挖窟而成的“七尊佛像石窟+玉皇大帝像”的左右石窟石刻,我迷茫了!一块巨石石窟完美体现了两种思潮、两种信仰、两种文明,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?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山西壶关沙窟村的古圣山巅?然而,历史只呈现了结果,却没有告诉原因。
我查阅了手边可能查到的资料,没有找到令我满意的答案。我只知道,北魏孝文帝接受汉族先进文化,促进了民族的融合,但当年地处内陆太行山高地的沙窟石窟的“工程项目”负责人,又是如何高超领会孝文帝的旨意,以“一石两窟”“一石两像”“一石两文明”的方式体现“圣上”旨意的?而类似这样的石窟,在全国现有的石窟中,较为罕见!
如今,这样的故事仍在传诵: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,至上党的壶关巡游,见壶邑东南百仞山峰,通天屹立,巍巍壮观,钟灵毓秀,祥光四溢。谓左右曰:“莫非玉皇大帝居此也?”左右奉承曰:“观其景,实为罕见,即非玉帝居此,也属玉帝之辖,何不为玉帝建宫焉?”孝文帝感慨系之,遂拨银两,命人在古圣山巅向下掘窟而雕七佛及玉皇大帝像……
千年的传说,百姓口口相传,越传越真,越传越信。但我作为文化学者,谨慎相信。我查阅了相关的历史资料,我知晓,北魏王朝在经历孝文帝拓跋宏的爷爷太武帝拓跋焘大规模“灭佛”,其父亲文成帝拓跋浚“兴佛”运动之后,心怀“仰光七庙,俯济苍生”之志的孝文帝,逐渐意识到“单靠外来的佛教无法臣服朝野,唯有兴佛教而不压制道教,方可兴国服民”的道理。孝文帝推行汉化的过程,就是推进“佛”“道”兼容、“佛”“道”并兴的过程。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轮“洋为中用”“中外并举”“兼容发展”之先河。而地处内陆山地的沙窟村的古圣山玉皇七佛庙的石窟,正是完整体现孝文帝这一思想的最好例证!从这个意义上看,沙窟石窟远非云冈、洛阳等地石窟之可比!
北魏至今历史学上的年限大约有2500年,但为什么那时候这块巨石石窟又被掩埋?我又查阅了史志书籍,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记载。而同时期的大同云冈石窟、洛阳龙门石窟等却存续得相对完好,教徒及信众云集如盖。当年,在沙窟村古圣山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,将刻有佛像与玉皇大帝像的巨石石窟掩埋于地下?
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,就这样以“断年断代”的方式,呈现在2500多年后的我的脑海中。连续好几天,我都在围绕这一“千古谜团”而思索、探究、猜想!妻子甚至说,我探究玉皇七佛庙的北魏石窟“走火入魔”了。
我强烈地认为,现存的史志书籍对历史事件的记载,也不一定客观、真实。基于此,对湮灭于历史长河、无任何记载、无任何线索的历史事件的猜想,与真实历史的吻合度则更低。但行文至此,我还是不得不对这一事件基于我的历史认知,去猜想这块巨石石窟被掩埋的可能性原因。我认为:很可能是某个年代,当佛家与道家在古圣山发生了无法调停、无法“共存共生共荣”的局面后,佛家与道家争斗的结果!也就是佛教信徒与道家信徒对垒、打斗的结果。争斗、打斗的结果就是毁掉、埋掉巨石石窟,让古圣山佛家与道家信徒无法再前来朝圣朝拜,从此,被北魏孝文帝看好的一方“圣境”,变得一片静寂!
就这样树木与时光同长,山石与岁月共生,朝代更迭至元朝五年(公元1268年)前后,沙窟村古圣山被填埋1200多年后,首次有了“官方”的消息:据2008年编撰的《太行山大峡谷志》中所载《重修玉皇七佛庙记》(元∙韩仲元):
自壶关县治之南二十五里所,有聚落曰沙窟,其西土山曰古圣。面炎帝之祠,背紫微之胜,翠屏右峙,诸峰环合,每凭高寓目,胜概可尽,是诚一方秀绝之地。兵荒而后,本村都统牛成之甥路仲平,小字福童,泽州解庄人也,忘形落魄如为神所凭依者,日于其处凿地运土,而为以为劳。岁余,得巨石,高约一丈五,广阔如之,其下石室二所,东西相背,左玉皇,右七佛,石像俨然,于是饰以金碧,处则构以檐楹。凡乡民之祈请者,雨阳疾疫,无不如愿……
此碑记的撰写者韩仲元,为元朝初年壶关县衙的“教谕”。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兼文化局长级别的官员,所撰写的碑记中也没有具实、具象、具真记载重新开挖沙窟石窟令人信服、客观真实的过程,而是假一个外乡人“路仲平”,以“忘形落魄如为神所凭依者”之态,使石窟得以重见天日的“神况”,并且还达到了“求雨求生求功名有求必应,解灾解难解忧无不如愿”灵验之境。

此后的700年间,玉皇七佛庙迎来它兼佛兼道活动场所的“高光时刻”:庙宇于至元十六年动工,十八年竣工,庙宇扩建占地20余亩,房屋百余间,分布院落共8所,分别是:玉皇大殿、七佛殿、牛王殿、虫王殿、三宗殿、奶奶殿、中戏楼殿、西戏楼殿等。也正是这次扩建,才使玉皇七佛庙有了数百年的“香火传奇”。清朝年间,康熙帝还亲笔为玉皇七佛庙题写门头匾“昊天上帝”,至今仍悬挂于庙门上方。百姓口中传诵的玉皇七佛庙的故事很神奇、很玄妙,我只是作为旁观听众,求证历史学者,不持肯定与否定的观点。但有一点,这些故事中都充满了百姓对美好、善良、安平、康健的祈盼和祈福,不妨列举一二。
明朝天顺年间,沈藩庄幼埒镇守上党时期,相传皇城宫门上有一个腰闩上会出现水气聚珠现象,庄王令工匠将腰闩雕成一尊玉皇大帝神像,送到沙窟村玉皇七佛庙内供奉,每逢天旱之年,祈祷甘霖,非常灵验……
又闻,某年上党某村某年夏天天旱多时未雨,一众乡亲来玉皇七佛庙心诚祈雨,脱鞋赤脚进殿叩拜,返回途中,不慎将所祈雨水洒于楼峰山下一村庄,结果此村倾盆大雨即刻临降,一众乡亲不得不又来求雨,方使其村庄及时雨落下……
又闻,某年夏天,古圣山一带50天未有降雨,地里庄稼卷叶燎尖。某日,玉皇大帝给村里长者托梦:若将暂放在东沟里破窑洞的“出驾玉皇大帝”送回玉皇七佛庙,塑身批彩,诺三日天降透雨,滋润庄稼。村里长者立即行事,果然灵验……
行走在村里,走访在农家,关于玉皇七佛庙“灵验”的传说,百姓开口可讲。我总在想,这算不算最纯粹、最地气、最原生的“中国传统文化”?而这种说不清、表不明、写不出的文化,却真实存在了几千年!它对淳化乡风、古朴民风、引良家风是否起到了最基础的功效?
1950年代,玉皇七佛庙的正殿被拆建为“壶关三中”,办学至1980年代初结束。庙内现存建筑,改建维护年代不一,但玉皇七佛庙的文物学、文史学、传统文化学的价值,正在被重新关注。2023年4月底,县文管部门派来了测绘专业队伍,对整个庙宇进行着抢救性数据测绘,我们期待有一天,修缮一新的玉皇七佛庙会以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!
打锅“牛”生生不息的家族故事
“问我祖先来何处?山西洪洞大槐树,问我老家在哪里,大槐树下老鸹窝”。这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怀念故土、表达乡愁的俗语。生而为人,对故土亲人的怀念之情,是每个人深入血脉的记忆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在沙窟村的古老历史中,竟然发生了一个载入中华姓氏故事、令百姓口口相传、被众多文献书籍记录的打锅“牛”的家族故事!

连日来,我通过实地走访、问询百姓、查看书籍,了解到发生在沙窟村打锅“牛”的传说,主要有两个版本,尽管这两个版本故事发生年代相隔1100多年,但都很原委地记录了这个故事。
相传,沙窟村发现石窟的路仲平之舅牛成,为沙窟村牛氏之祖,其祖先为陇西郡(现甘肃省定西市)人,后在明朝官拜为丞相,他体察民情,颇受百姓喜爱,人称牛丞相。为使皇帝体察壶关三年大旱无雨、百姓食不果腹的灾情,将壶关地名编成了24个奇妙景观歌,曰:
壶关有个栲栳山,举手就能摸着天,如果要是够不着,脚底垫上半块砖,瓜掌有个小扁桥,桥上安着24个金驳条。登上风则岭,一眼望见三座城。仙城神池无极池,处处都是好风景。口头塔店巍巍池,南北行头连掌池。石坡安口盘马池,大河桥上杨家池。鹅屋柳泉二土池,南关刁掌小苇池。东西王宅录百池,淙上赛里龙君池。东西归善黄野池,川底禾登四家池。打开石门看水池,铜帮铁底燕的池。
皇帝听后,龙颜大悦,遂驾临壶关赏美景,但皇帝所见与牛丞相所言大相径庭:三年之旱灾,壶邑满目苍夷,饿殍遍地,何有歌中美景见?顷刻龙颜大怒,以欺君之罪将为民请命的牛丞相治罪并问斩。但皇帝此行也看到壶邑百姓因灾食不果腹之真相,遂下诏免壶邑三年税捐,使苍生得以喘息。
沙窟村牛氏族人闻听牛丞相被治罪问斩的消息后,连夜外逃。为使以后相聚有证,就将院里一口大铁锅砸碎,18个孩子各带一片锅片出走他乡……打锅“牛”的故事至此形成,并传诵千年。
近年来,牛氏后代相继从河南密县、鄢陵、滑县、武陟、林州、卫辉、临颖、安阳等地的牛氏家谱中发现,其中有不少家谱中明确记载:“源于上党沙窟村”。至今,河南省开封市南关村还保存有当年打破铁锅拿到的“锅片”。1990年代以来,这些当年逃离的打锅“牛”的后代,又陆续多批次返回沙窟寻亲认祖。浓厚的“根祖文化”氛围,形成了沙窟村独有的特色,与打锅“牛”相关的故事被不少书籍、媒体收录、传播。2023年清明前后,又先后有4批次的打锅“牛”后人返乡认亲祭祖……

建于元朝的中华牛姓祠堂“家佛堂”,是如今中华牛姓建筑最早、保存最完好的祠堂,在历经700多年风雨洗礼之后,依然屹立古圣山脚下。祠堂院中,当年由牛丞相从高丽(朝鲜)带回来的银杏树依然枝繁叶茂,挺拔入天,它们共同见证着打锅“牛”的后代生生不息、代代兴旺的家族传奇!也见证着沙窟村这个历史古村,厚积薄发、蒸蒸日上的良好景象!
癸卯年的春夏,天气忽冷忽热,我行走在沙窟村的街巷、角落,我的脚下就是当年这个悲壮凄惨故事的发生地!我在想:牛丞相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吏,尚有不惜“官帽”怜“民命”之担当,为民请命献己命之壮举,在今天,是否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?
当这个打锅“牛”的故事被百姓传诵的时候,我又听到另一个版本的讲述,同样惊心动魄!并且还有多块出土于沙窟村的唐代牛氏家族墓志为证。历史,从来都不会以一个“面孔”呈现在后人面前,许多历史的本原,都变成了“人为书写”的历史和“不真实”的历史。而后人又如何去分辨哪个是真正的历史,哪个不是?
前些年,我曾用心研究过三国的历史,当我仔细阅读、比对了各个版本的三国史志书籍后,我放弃了和自己较劲的深入研究。认为,所谓的“历史”就是一种说法而已,就如今天传诵的打锅“牛”的故事一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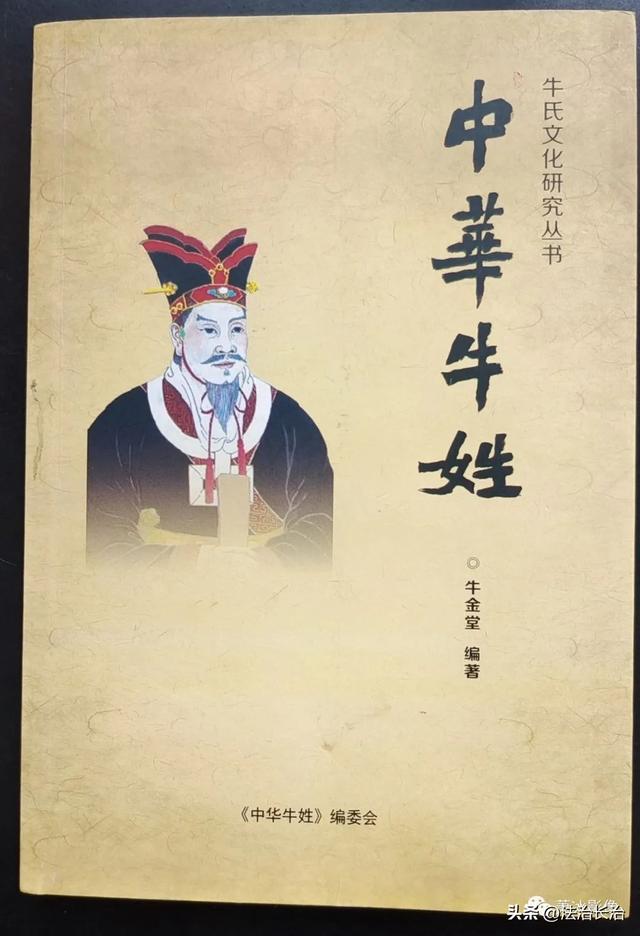
据牛金堂先生编著的《中华牛姓》一书中记载,沙窟村牛氏始祖为牛金(约190-250),自公元四世纪初曾任上党郡守,后随曹仁镇守荆州。史书记载,汉献帝建安十四年(209)周瑜领兵数万攻打曹仁镇守的荆州,牛金率领敢死队300人出城迎敌被围。曹仁奋力解围拼死救出牛金,尔后合力反攻,击退吴军。牛金因此役作战勇猛而崭露头角。后在魏明帝太和五年(231年)至景初二年(238),牛金又随司马懿征蜀、平辽东公孙渊反叛,因战功显著,官至后将军。

正始十年(249)正月,司马懿剪除了朝中最后一个政敌曹爽之后,站在了自己人生的巅峰,权倾天下。因当时民间流传谶言“牛(金)继马(司马懿)后”,引起司马懿的过度警觉。嘉平二年(250)司马懿迫不及待地赶在自己辞世之前,用特制的“鸳鸯酒壶”,分别储藏好酒和毒酒,请牛金赴宴,结果牛金被鸩酒赐死。
牛金死后,沙窟村的牛金家族,纷纷外逃。为便日后相见,将家里的大铁锅砸碎,分别带着铁锅的碎片逃难他乡。牛金死后,狠毒的司马懿为从根上破坏牛氏祖坟的“风水”,使牛金后代再无翻身之日,便派出军队将位于沙窟村的牛氏祖坟挖了一条宽20米、深20米、长3000米的大壕沟,如今这处大壕沟仍在。
但后来发生的事,谁都无法料到:司马懿之孙琅琊王司马觐的妃子夏侯氏与府中小吏牛钦私通,生下了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,还是验证了“牛继马后”的谶语!该事件最早被记载于东晋孙盛的《晋春秋》一书中,其后《晋书.元帝纪》《宋书.符瑞志》等书中也有记载。我无法判断这样的史书中记载的故事的真实性,但必须承认其中的戏剧性!对于崇尚真善美、相信因果报应的民众来讲,这样的结局实在大快人心!“牛继马后”这个古典成语由此形成。
据沙窟村资深乡土文化人、现年84岁的张国有先生讲述,1960年代,村东一户村民盖房挖地基时曾挖出过牛金之墓,坟墓里尚有牛金使用过的刀枪及墓志碑等,今已不知去向。以我之历史认知去理解,打锅“牛”故事发生的前提是,沙窟村的牛氏家族被官府追杀,被逼外出逃生,那么牛金死后,哪还敢有牛氏家族之后人公然运回牛金尸骨,安葬于本村区域?我分析,这种可能性极小。1960年代,如果村里真的发现了牛金的坟墓,也很可能是牛氏未逃走、或者外逃后又返回沙窟村的后人为感念祖恩,为牛金修建的“衣冠冢”!顺着这样的历史推断,就完全可以断定,司马懿发起的对牛金家族的“灭族”追杀并未奏效:牛金家族有的持铁锅片远走他乡,有的等事态平息或朝代更迭后,又重返故土沙窟,繁衍生息至今。2000年前后,在沙窟村地域发现多块唐朝的直接载明“牛金之后”牛氏族人的墓碑志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连续10多天的高强度撰写,使我沉浸于丰厚而久远的沙窟古村历史之中。此文收笔之时,已是凌晨三时,古圣山林地的野鸡,已在呼唤黎明的到来。我努力想站起来,但是,我努力地站了3次,也没能从椅子上直起腰来!这天,连续16个小时的伏案,已使我的“中年之腰”无法承受长时间写作之累!但我心里明白,进驻沙窟村,没有部门或人安排我文创这篇超万字的图文,但作为壶邑本土的文化人,既然我的生命有一时段在古圣山下的沙窟村度过,面对这个历史文化相当厚重的古村,我必须这样去行走、去写作、去拍摄才能对得起自己的本心!
我必须站起来,去迎接新的崭新的黎明!!!
文章来源于萧冰影像 ,作者平晓斌
来源 | 萧冰影像
编辑 | 李佳悦
责编 | 杨瑾
 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1854号
鲁公网安备37020202001854号